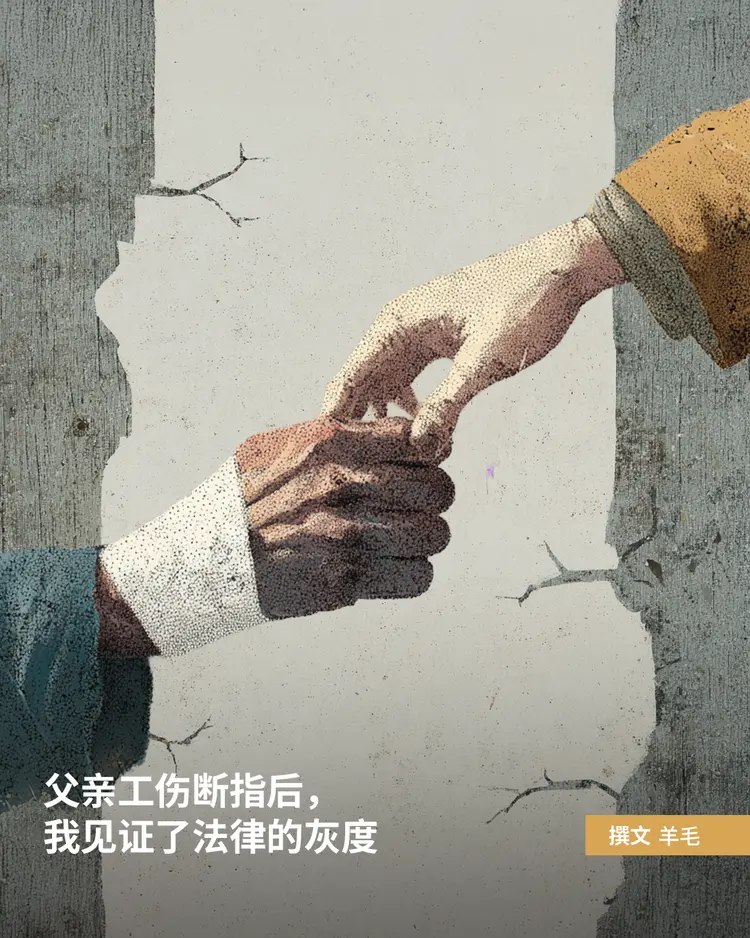劳动者专栏|父亲工伤断指后,我见证了法律的灰度 手机网易网
来源网站:m.163.com
作者:
主题分类:劳动者处境
内容类型: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
关键词:工伤, 用人单位, 父亲, 工厂, 人事, 维权
涉及行业:纺织/服饰/家具, 制造业
涉及职业:蓝领受雇者
地点: 江苏省
相关议题:工人仲裁/起诉, 工作时间, 工伤/职业病, 肮脏或危险的工作环境
- 作者父亲在工厂工作期间因操作电动台锯受伤,导致拇指截断,事发后工厂未主动为其申请工伤鉴定,且对赔偿态度模糊,推诿责任。
- 父亲入职时被要求签署放弃社保的合同,工厂未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,后续维权过程中该合同成为赔偿争议的主要障碍。
- 父亲长期超时加班,受伤前三个月每月几乎只休息一天,工时严重超标,但工厂并未为此支付法定加班费。
- 工伤发生后,工厂仅以“人道主义”为由提出低额赔偿,未按照法律规定承担工伤赔偿责任,协商过程不透明且以“老板同意”为借口拖延。
- 作者作为家属代理父亲维权,发现工伤赔偿流程复杂,法律规定与实际操作存在灰色地带,劳动者维权难度大。
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,仅供参考,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。
编者按
本文作者自称是“被家人托举出来的幸运儿”。作为农村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,她大学毕业后生活在城市,没有多少机会了解农民工父母的生存处境。直到去年,她的父亲在江苏一家家具工厂失去了半截拇指,面对工厂的推诿,和一份父亲入职时无意间签署的“放弃社保”的合同,她代理父亲的劳动争议案两次站在仲裁庭和法院法庭上。这次维权经历,令作者窥见了底层农民工的生存状态,立法的嬗变,以及司法系统的灰度。
前往Substack平台订阅水瓶纪元
https://aquariuseras.substack.com/
或将您的邮箱发送至后台
8月27号,等了一年两个月,父亲断指的第一笔赔偿终于到账了。
通过代理父亲这起工伤维权案件,我第一次知道法律不是黑白的,而是在中间的灰度里撕扯,我也知道了法和情无法真的分得清。我们幸运地赶上了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发布的,其中明确了用人单位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责任,这给父亲的案件带来一丝曙光。与父亲并肩战斗的日子里,我直观地体验到了掩盖在时代发展褶皱里的底层伤痕。
父亲失去了手指
我是在父亲受伤5天后才知道这个消息的。
2024年6月的一个周一,父亲意外受伤。此前每天我都会给家人打视频电话联系,但在那一周,他们出奇地安静寡言。起初我觉察到了不对劲,接视频的主要是弟弟,但他仿佛不是很想和我说话,表情也比平时沉闷,父亲和母亲则都较少出现在屏幕里。
家人们知道那一周我很忙。我在准备在职硕士毕业论文的预答辩,白天工作、晚上写论文。直到周六完成答辩,在又一次欲说还休的电话中,我才知道父亲在工作期间受伤了。
父亲探了探头,出现在屏幕的角落。他不到60岁,头发几乎掉完了,近乎一个光头,出租房客厅灯光昏暗,照得脸色不好。父亲的牙齿也几乎掉完了,他瘪了瘪嘴,想开口说话,又退缩了回去。母亲说,“你爸受伤了”,还没等母亲详细解释,父亲紧接着说,“不用操心,没事了”。
后来,通过父亲的口述、一系列的工作记录、事故现场证人证言,我大致还原了受伤的过程:周一下午2点左右,父亲在工厂里使用电动台锯切割木材,不慎被割断了一节大拇指。照片显示,车间里很杂乱,堆满了大块木材和大型器械。父亲自己带着流血不止的手找到主管,主管联系人事安排车辆准备将父亲送往医院,等车的过程中,其他工友看到父亲受伤,上前帮忙止血。父亲自陈,直到那时候,他才开始感觉到疼痛、发晕。
作为维权证据之一,父亲拍的受伤现场照片存在我电脑里命名为《2024年6月父亲工伤》的文件夹中。我至今都不敢点开去看。
没有人调查父亲受伤的具体原因,我却不甘心。父亲年轻时是木匠,有娴熟的木工手艺,老家家里各种雕了精致花纹的木材家具都是他一手打造的。加入这间工厂不久,他就被“升职”负责切割木材工件,钉装各种形状的包装箱,用于货物的出海运输。按理来说,那都是父亲再熟悉不过的手艺活,他不至于这样“不小心”被切掉手指。
很久没住的老家,刷漆的地面和一套木质家具,是父亲30多年前亲手打造。(图_羊毛提供)
我核对父亲的工作时间,觉得不对劲。父亲刚到工厂时,每月工作24至27天,每月工时平均为204小时。这意味着他每天工作8至9小时,还算正常。但在他受伤的前三个月,他每月工作29至30天,每月工时从233小时到273小时不等,平均每天要工作接近11个小时。去年6月,父亲受伤时还在月中,他的当月工时却已长达134小时,他几乎每天都在工作,有时上足了12个钟的班。家人回忆,受伤之前的那段时间,父亲总是早上7点多出门工作,晚上10点多才回家,没有周末,强度更甚于996。
父亲有手写工作时间的习惯。2024年4月,他工作了29天,共计273.5小时。(图_羊毛提供)
受伤前三个月,父亲每个月仅被安排休息一天,分别是4月4日清明节,5月1日劳动节,和6月10日端午节。这仅有的三个休息日看起来是为了避免高额加班费,“不得已”给父亲放的假,因为按照《劳动法》,工人如果在这三个法定假期上班,工厂要支付三倍薪水。
这段话,我本想作为陈述意见拿到法庭上说的,但最终没有机会去提。我不知道如何论证超长的加班时间和工伤之间更直接的联系。
父亲受伤后,先被送到了工厂最近的小医院,医生告知骨头断了,小医院接不回来,建议马上转去骨科比较好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,看看还有没有希望。送到上海六院后,手指头也没有接回来。
在上海做完“拇指残修手术”的当天,父亲就带着药品回了家。为了不给我在工作和学业之外增加压力,此后五天的的视频电话中,他、母亲以及弟弟都向我隐瞒了伤情。我是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,在只有小学和初中学历的父母心里,我的学业和职业发展甚至比他们自己的健康更重要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,不论是父亲被客户长期拖欠工程款,还是母亲动手术,他们都不会第一时间让我知道。父母盼着我读上好大学,留在大城市,过上和他们不一样的生活,我做到了,可是这却让我和父母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。
那个周六,在电话里得知父亲已经受伤一周,我懵住了,挂完电话以后我大哭了起来。
被拖延的工伤鉴定
得知父亲受伤的第二天中午,我赶回了一小时车程之外父母居住的地方。父亲剩下的小半截拇指被严严实实地包扎着,从外面已经看不到血迹了。父亲很乐观,他说再过一个月伤就好了,就可以回去上班了。父亲琢磨着工伤赔偿,他在手机短视频软件上搜索,预估自己因伤致残的程度有九级,他告诉我,有的短视频告诉他,像他这样的伤情,厂方可以赔到十几万。
父亲还告诉我,工厂主管上周三曾来家里看望过他。主管让父亲不要声张,慢慢养伤,承诺伤好了他就能回去上班。
我那时完全不懂相关法律,甚至不会仔细看自己的劳动合同。当父亲受伤之后,我只有一个直觉——这可能需要做工伤鉴定,但我没那么相信短视频平台。我又想起来前几年认识了一位工友,年龄和我相仿,对于和工厂、雇主打交道有自己的一套经验,我曾请教过他伤残工人就业辅导、办公室职员打卡规定等权益问题。我决定再次向他求助。
这位工友很快在微信里回复了我,在纠正了我对工伤的一些误解之后,他对父亲的情况提了一连串的问题:有没有社保?有没有劳动合同?工资怎么发的?年纪多大?伤到哪里?这一连串提问让我有了思路,我决定先从核查父亲在工厂的工作情况、合同情况开始。
工厂的一些做法让我有些隐忧:比如主管上门时给了3000块钱,让父亲不要声张;人事用“意外保险要到期了”为由,甚至不确定能否帮父亲报销点医疗费。工厂不透明、不一致的态度让我觉得不对劲,我参照自己的工作经验,认为应该有相应的程序让父亲合理申请休息、医疗费和补偿。我担心可能会因为这些事情要和工厂拉扯,搞不好还得维权。
我给父亲和工友拉了微信群,介绍他们认识。工友给父亲的第一个建议是:一定要去做工伤鉴定。我在那时候才知道,工伤鉴定有两种,一种是雇主为受伤的工人申请鉴定,当雇主不履行这个责任的时候,则需要工人自己去申请。这时我们才意识到,尽管工厂的人事主管和生产主管有和父亲沟通过,但都以安抚为主,全然没有提及要给父亲申请工伤鉴定。而这时,距离父亲受伤已经半个多月。
接下来工友建议我们两手准备,一面和工厂协商,一面去了解本地的鉴定流程。起初,我们对父亲的案件很有信心,因为父亲和工厂的劳动关系事实清楚,因工受伤的过程清楚,企业没有给父亲缴纳工伤保险的事实清楚,按流程走下去,申请全额的赔偿看似没有问题。但在接下来索赔的过程中,我们经历的困难却远超预料。
一份放弃社保的合同
自受伤后,父亲在家被动地等了两个月,期盼着工厂的下一步安排。这期间,工厂人事和生产主管陆续和父亲通过几次电话,也请父亲去公司面谈过一次,但始终不愿意透露赔偿意向,对于父亲的赔偿诉求只说“钱是有的,但不要和别人说”。
沟通过程中,当工厂发现我们已经了解了一些工伤处理的规定,就开始在工伤赔偿标准上和我们绕圈子。人事主管一面说,赔偿金额根据年龄定,年龄大就要少一点;一面又强调,因为没有做工伤鉴定,不能按照某一级的标准来。谈了半天参考依据,人事主管又提出,“要看老板同不同意”。本来有法可依的赔偿,在协商中又没有了“依据”,最终变成“老板说了算”。
父亲最初的期望是9万至10万块的赔偿,有意愿协商,并且想回去上班。从老家搬到苏州的七年间,为了养家,父亲开过滴滴共享车,去过工地,进过厂,几份工作的辛苦程度和收入都不相上下。最近两年,随着岁数增长超过了许多岗位的年龄限制,父亲的选择越来越少,经济下行也让情况变得更加艰难。找到这份工作之前,父亲已经至少遭遇了2次在网上找工作被骗,一次是骗他贷款买面包车做货运,另一次则是骗他去昆山,到了昆山,骗子让他交了体检费、中介费,之后就杳无音信,报警都没有用。
这份切断父亲手指的工作,能让他发挥木工方面的手艺,还让他颇有一些成就感。“先是木工钉包装箱子,后来上锯做一些有难度的事情”,在维权微信群讨论起工作内容的时候,父亲分享了一些他切割出来的木材的照片,那些是类似榫卯结构的木头构件,切割得规整漂亮。父亲说起这些工作的时候滔滔不绝,难得地变得很有分享欲。
父亲在微信群分享自己工作期间做的木质构件(图_羊毛提供)
直到今年4月在仲裁庭出庭答辩,我才发现工厂与父亲签的制式合同中,有受聘方主动放弃社会保险的条款。我懊悔不已,前期准备很久,却没有仔细看懂这一条,导致工厂在仲裁庭提交这份我早已有的证据时,我却没有做任何相关的答辩准备,在庭上措手不及。回家以后,父亲和我回忆签合同时的情况——那是入职第3天,主管拿着两份合同到车间让他签字,并告诉他“工人签的合同都是一样的”,父亲因此没有查阅,直接在车间工作台上签了合同。
和大多数老一代的农民工一样,1960年代出生的父亲没有社会保险的概念。他这辈子没交过社保,也没有人告诉过他,用人单位有义务缴纳社保并承担部分成本,这是对他遇到意外、就医、养老的保障。父亲的逻辑很简单,一句“和其他的工人一样”,就足以让他放心了。
这份有父亲签字的合同,成为此后我们维权的最大挑战。在法律层面,《社会保险法》和《劳动法》早已明确,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并缴纳社会保险费,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同时履行的法定义务。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均不能随意处分这项权利,任何形式的“不缴纳社保”约定都是无效的。
在司法实践中,对不缴纳社保条款的无效性认定相对统一,但是对其法律后果,观点却存在分歧,也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情况。在江苏地区,有的仲裁委和法院认为即使该条款无效,也不可完全归责于企业,当出现纠纷或我父亲类似的工伤情况,劳动者不能以此为由要求相应补偿。全国来说,部分地区会支持劳动者获得全额赔偿,部分地区会支持劳动者与企业在赔偿责任上“三七开”。江苏地区判罚标准不一,我找到了最近2024年无锡的一份判决,支持了劳动者的全额赔偿,其他则多对劳动者不利。
到了2024年8月下旬,父亲断指两个半月后,工厂人事约了我和父亲一起去面谈。我们经过父亲工作的一楼车间,那里响彻着电锯、叉车的器械声音。走进二楼的会议室时,父亲小声说,“老板在这呢”。我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和工位上的人说了几句话,就进了另一间独立办公室。
我们坐在透明玻璃墙的会议室里,父亲和我坐一边,人事和生产主管坐对面。之前电话里,他们说“要和老板谈”“要老板做主”,于是父亲首先低声询问:“老板来吗?”人事回答:“老板忙得很,我们谈。”
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与父亲共事的工厂管理人员。人事主管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多少,是一个瘦瘦的女生,头发过肩,穿着简单;生产主管也是个穿着朴素的中年男性,戴个眼镜,皮肤黑黑的,身材中等偏瘦。他们看起来和普通工厂员工没什么差别,我想起父亲与人事通话时说的话:“都是出来打工的,没有谁要为难谁的意思。”
这次的见面,我们聊了将近1小时,看起来工厂此前从未像这样正式处理过工伤。我听父亲提过,厂里之前有过数起工作中员工受伤的情况,要么是少数有社保的员工拿到社保基金的赔偿了,要么就是私了了。我们认为,企业没缴纳社保有过错;工厂则强调我们已经放弃了社保,“工厂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才协商赔偿”。我曾从事公益工作,工厂代表这样提起“人道主义”,令我觉得刺耳。工伤赔偿原是工厂要承担的责任,对方那样说起来,仿佛是对受伤工人的额外恩赐。
在那次沟通中,我们第一次了解到工厂当时的赔偿意愿是3万块。当时生产主管说漏了嘴,说他个人觉得“师傅你这样的情况,(工厂)赔5万也是没问题的”。
父亲与我
父亲和我决定走法律程序维权。
2024年8月22日,面谈的第二天,人事主管通过父亲留的紧急联系人电话单独加了我的微信,说想要和我聊一聊。主要目的,是希望免除掉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两个赔偿金额的大头,这两笔钱占了预期14万元赔偿金额中的7万5千元。而另外的赔偿项目和工伤等级有关,因为我们还没有进行工伤认定,人事不认可我们预估的九级赔偿依据。
我心里产生了一种紧迫感,面对拿着“要和老板谈”做挡箭牌、处置不透明的工厂,工伤认定迫在眉睫,和工厂的劳动关系的处理也不能再拖下去了。
面谈前后的那几天,我、父亲和帮忙的工友每天都在群里讨论,比如如何回复工厂、如何准备工伤认定等等,因为涉及到越来越多的法律规定,学历不高的父亲逐渐减少了讨论的参与。此时父亲已经历了数次由他直接面对的无疾而终的协商,他越来越希望由我去和人事沟通。
我开始成为父亲工伤案件的代言人。一方面是人事已经直接找到我,另一方面工友给我们的建议是,案情脉络简单,我作为直系亲属代理完全没有问题。父亲相信,读书成绩好的我能理解这些法律,去和人事周旋,他唯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占我太多时间、给我额外的压力。
那几天的进展很快,人事加我微信主要目的是想私了,并透露如果我们坚持全额赔偿,他们也可以补缴社保来规避此前的部分违法情况,暗示我们不能再拿工厂违法说事。未缴纳社保,是工厂最明显有违法规的行为,虽然实际上,工厂还有安排超时加班、未支付加班工资、未提供劳动保护等其他违法行为。
和人事沟通第二天,我们向工厂发出《迫使辞工通知书》,以工厂有多项违法过错为由,正式解除和工厂的劳动关系。但仲裁庭不承认这份材料,他们认为用“不缴纳社保”作为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的主要理由并以此申请赔偿不成立,依据还是父亲已在写明自愿放弃社保的合同上签了字。
我花了一天时间修改这份通知书。当我一字字敲出父亲面临的艰辛时,不断回想起来他坎坷的一生。90年代,父亲20多岁时,就当了小镇上的建筑工程包工头,虽然业务不大,在当时算能挣钱的,那是他意气风发的十年。父亲30来岁时,我刚出生的弟弟重病,他自己又经历了严重的摩托车车祸,这一连串打击下,我家的生活再没有起色。尽管我随着升学开始往外走,去县城里读寄宿高中,再到北京求学,而后定居苏州,但父亲、母亲和弟弟都停滞在了农村老家。
农村老家,我家屋后的池塘和菜地,几十年都没有变化。
(图_羊毛提供)
遥远的仲裁庭
申请工伤认定的结果花了2个月,认定完工伤之后,我们又开始做伤残等级鉴定,拿到鉴定结果又另外花了2个多月,接着再等了15天,以确认工人和工厂均无异议。一转眼已经2025年春节了。
在家等待的时间过于漫长,父亲意识到回不去以前的工厂了,提出想找点事做。父亲有手艺,工友建议他注册一个“鲁班到家”的账户,拎着工具箱就可以去帮人维修、做点手艺活,可是因为父亲已经超过55岁,实名认证都过不了,父亲对这些新兴的零工平台逐渐失去了尝试的兴趣。
他甚至想念在工厂朝7晚10的生活,因为他可以不用离家太远,“晚上在家的(工作)好一点,有家的味道”。父亲大半辈子都在工地上度过,有时候长时间和家人分居,有时候带着妻儿住在工地,回到家里吃晚饭、睡在家里的床上,可能是他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。
父亲再次进了厂。那时据他受伤已经4个月,断指的伤口已经愈合,只是还有一些刺痛感。这一次是一个食品加工厂,父亲去做简单的包装工作,工作强度低一点,但工作时长与之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,也几乎没有什么劳动保障。因为时薪低于之前的技术工作,父亲更加期望可以加班了。
看到父亲仿佛从一个火坑跳进另一个火坑,我有时怀疑起维权是不是对的选择。决定维权——失去工作——等待赔偿的漫长过程——拉扯谈判——跳进另一个岗位的火坑,这个结果会比不维权好吗?我质疑自己拒绝私了的决定,如果不维权,父亲是不是还有机会回到之前的工厂,做让他有成就感的工作?
过了正月十五,父亲给工厂人事拜年,并询问工厂的赔偿预期——他几十年的工作习惯是,“正月十五之前不讨钱”。这时父亲的工伤报告已经出来了,他的受伤情况被鉴定为致残八级,赔偿金额参考标准更高。工厂把愿意私了的金额提高到了8万5千元,也终于开始按有明文规定的工伤待遇计算,而不是只说“老板说了算”。
这时距离父亲受伤已经8个月,我们为维权投入了大量的精力,对工厂的信任感也已消失殆尽,于是坚定地走了法律仲裁程序。
这是AI根据真实照片生成,朋友们和我模拟仲裁出庭的场面,大家用这种方式帮助我面对未知。(图_羊毛提供)
准备好仲裁材料后,父亲开车带我去远郊的仲裁委员会提交了立案申请。父亲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小城市,但是仲裁庭远在30公里之外,我难以想象一个受伤的工友,如果要乘坐公共交通,得花多久时间来到这里。整个接待处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在接待立案,她的桌面上已经堆满了案件资料。
从提交材料到出庭,又过去了快2个月。出庭日排到了2025年4月17日。开庭当天,父亲曾在含有放弃社保条款的违法合同上签字的情况,成为我们的案件中唯一有争议的部分。我认为合同本身违法,放弃社保应属无效。但在中国的部分地区,仲裁庭、法庭都倾向于认为这份“签字”是劳动者的真实意思表达,不接受其经济赔偿和部分工伤赔偿的诉求。
不出预料,仲裁开庭一个月后,我们得到了一份倾向工厂的判决结果——我们主张的全额工伤赔偿、经济补偿都没有被支持,赔偿金额维持在了8万5千元。
我在仲裁庭外拍摄的照片(图_羊毛提供)
这时,断指对父亲生活的影响也逐渐显现出来。他失去的是功能性右手拇指的一大截,正是我们普通人吃饭捏筷子的那部分指头,这意味着他在吃饭、喝水、刷牙等日常生活里都会遭遇阻碍,更不用说对于他工作能力的影响。
政策的转向
2025年5月底,我们对仲裁结果不服,提交了一审的起诉状,正式进入法院诉讼阶段。
进入法律流程,我面对的却是在保护劳动者权益上,司法系统内部混乱、不堪重负的一面。提交仲裁材料和起诉材料时,我们都没有拿到立案回执,这就意味着限期办理的规定完全无效。我想起之前在仲裁庭里,工作人员桌面上堆积如山的案件,忍不住感慨,大多数想要依法维权的人根本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。
有经验的朋友告诉我,要一直打电话去催司法进展,甚至要摆出“泼妇闹事”的姿态,才可能有效。而法院的电话,在很多情况下都打不通,我至少给法院打过超百次的电话,接通的次数两双手就能数得过来。每次打电话前我都要先做思想准备,不知道该强硬、无赖一点,还是理性、容易沟通一点。因为对司法系统缺少了解和信任,我害怕和对面的法官、工作人员沟通不当,会影响父亲的案件判决。
父亲的案件终于定在2025年8月4日一审开庭。
7月中旬,有法院工作人员找我询问调解的可能性。这时我心里只剩下三成胜算,甚至被磨得有点畏惧上法庭,抱着调解成功的期望在等待。7月30日,我收到了开庭传票和对方的答辩材料,庭审按原计划进行。这意味着调解程序没能再推进。
我在对方的答辩材料上,看到工厂请了当地一间比较大的律所的两位律师代理出庭。此前仲裁阶段,工厂和我一样没有请律师,只是让人事和生产主管代为出庭。我搜索到其中一位律师是前法院工作人员,这令我更加畏惧。
转机意想不到地发生了。8月1日上午,我在整理材料时,收到关注我案件的律师朋友和工友们转来(下称《司法解释》)新闻发布会的文章。这是刚刚发布的新政策,其中第19条明确指出: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,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,该约定或者承诺无效。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解除劳动合同,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,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。
朋友第一时间在微信给我转来《司法解释》的发布会文章。
(图_羊毛提供)
尽管这份《司法解释》要到9月1日才生效,但第19条规定对父亲的案子是有利的。8月4日下午开庭,我拎着两大袋的文件到了法院的庭审室。我给法官和对方律师分别提供了一份厚厚的补充证据,这些证据包括证明父亲工作时间待遇的不合理、工作环境缺少劳动保护、企业存在主观恶意等。
出乎我意料的是,当我交完补充证据坐下来以后,法官却开口说:“既然大家都到了,那先聊一聊吧。”庭审开始往调解的方向走,而且是有利于我们的诉求的。看来最新的《司法解释》还没正式生效,但已经决定了父亲案件的审理方向。
经过几轮谈判,父亲的案件最后按照调解的方式结案了。这期间省去了所有的陈述、辩论环节,我作为非职业律师,准备了每一个环节的可能应答内容,加上前一晚熬夜到凌晨3点的证据材料,全都没有用上。
我留意到,这份《司法解释》看上去对我父亲这样的底层工人有利,却在社交媒体上遭遇了一些批评。批评者认为,在利润率比较低的行业,诸如餐饮业,这份强调企业社会保障责任的《司法解释》,会让企业经营更加困难,而这背后,也许揭示了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更深层次的问题。
面对提高了强制性、一致性的《司法解释》,民间有批评更有对策。我添加过多位劳务中介为微信好友,在朋友圈的招工广告中察觉到了变化的重点。《司法解释》发布后,不论是民营工厂还是外资工厂,招工岗位描述几乎一字不改,但会增加一句“以上工资包含社保”,社保的成本以这种方式转嫁给了议价权低的工人。
一家民营灯具厂的招聘文案,在《司法解释》即将生效的背景下,招聘方在末尾增加了一句“以上综合工资包含五险补贴”。(图_羊毛提供)
如果不是父亲在工厂里失去了一节手指,我可能永远无法切身体会底层劳动者生存环境的艰辛。在父亲之前工作的那家工厂,员工唯一的保障是一份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和一份团体医疗保险。我核对《保险条款》里最严重等级的赔偿,要达到“如四肢瘫痪或者颅脑损伤导致植物状态、日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处于完全护理依赖状态”,才可能拿到最高20万的赔偿,这就是我父亲这般底层工人生命的定价。如果仅根据这些保险标准,凭我父亲“仅仅”断了手指,不够格拿到任何商业意外保险的赔偿。
最终,按照法院调解结果,父亲工伤八级将拿到15万元的赔偿,分两期支付。同时父亲要自愿放弃工伤争议案之外的诉求,如加班工资、社保补偿等,双方就本案争议一次性了结,再无纠葛。
在等待的这一年两个月里,父亲已经在新的工厂工作了半年多,一生害怕“手停口停”的他对辛苦加班的代价和社保的必要性依然没有清晰的概念。今年,我父亲已经59岁,等他60岁退休后,养老金预计每月100多元。这笔养老金意味着,父亲不可能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真的有机会休息,但职场上留给年迈父亲的工作岗位、保障都已越来越少了。
撰文_羊毛
编辑_滚木
平台编辑_cc
水瓶纪元原创文章,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
点击阅读原文,可前往Substack平台订阅水瓶纪元,或可在后台留下您的邮箱,我们将添加您至订阅邮件组。
⬇点击头像关注